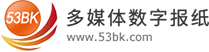本报记者 张小海
在山西北部,一座曾以煤炭能源闻名的城市正经历生态转型。朔州市,这片位于桑干河上游的黄土高原,多年来通过系统化的水环境治理,构建起资源型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范式。从河流治理到产业变革,从制度建设到人文重塑,这座城市以水为媒展开的绿色实践,为北方缺水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样本。
治理逻辑:从末端截污到系统治理
朔州的水生态治理经历了认知深化的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转集中于河道清淤、截污纳管等末端治理,但发现短期内水质虽有改善,却未能摆脱“反复治、治反复”的困局。第二阶段转向陆域治理,认识到流域问题需从源头破解:投资逾3亿元实施城区雨污分流改造,终结了合流直排水历史;清理河道垃圾10万余吨,消除沿河直排口217个。然而水体流动性差、自净能力弱的困境依然存在。
真正突破在于第三阶段的系统性治理思维:将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作为有机整体,统筹实施“上中游协同、干支流并举、水岸城同治”方略。在桑干河干流与源子河、黄水河等7条支流构建网格化修复体系:上游封山育林涵养水源,中游打造复合生态廊道,下游建设千亩人工湿地群。针对神头泉群这一华北重要岩溶泉,划定三级保护区严格禁采限采。这种整体性治理使水质达标率从初期53%升至100%。
“水的问题表象在河里,根子在岸上。”朔州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指出,“必须将治理范围从河床拓展至全域空间。”开展国土空间优化行动,调整工矿企业与水源地的空间分布,对采煤沉陷区实施地质环境恢复与植被重建,系统解决水土流失问题,从而保障了水生态修复成效的持久性。
制度创新: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构建
水生态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行政手段的局限性。朔州市创新构建“政府主导、企业担责、社会参与”的治理体系,形成多重制度保障:
跨区域协作机制打破行政藩篱。与大同、忻州建立“三市联动”机制,成立桑干河流域管理委员会,协调水量分配、污染联防等重大事项。创新实施跨市生态补偿:上游右玉县实施退耕还林扩大水源涵养区,下游应县对生态服务支付补偿资金,实现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的价值转化。
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刚性约束。全面推行“河长+警长+检察长+法院院长”四长联动,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。2023年办理涉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2起,追偿生态修复金800余万元。创新无人机巡航与水质自动监测站结合的智慧监管,实现全河段动态监控。
公众参与机制激发内生动力。在神头镇建立的“环保积分超市”,村民可通过收集河道垃圾兑换生活用品,每年参与人数超万人次。公开选聘民间河长186名,组建环保志愿者队伍32支,形成全民共治的社会网络。这种制度设计使生态保护从政府任务转化为群众自觉。
价值转化:生态资源驱动产业转型
水生态治理绝非孤立的环境工程,其本质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。朔州市将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同步推进,实现“绿水青山”向“发展动能”的持续转化。
绿色工业体系重构传统产业。在怀仁陶瓷园区,污水集中处理厂的中水回用率达85%,年节水300万吨。国能朔州电厂实施空冷技术改造,单位发电水耗下降70%。高耗水企业必须配套节水工艺,倒逼46家企业完成清洁化改造,形成节水与减排的良性循环。
特色农业崛起依托生态优势。在治理后的盐碱滩涂,发展水稻立体种养2万亩,“朔稻香”有机米亩产值提升3倍;神头泉域建成千亩冷水鱼养殖基地,虹鳟鱼年产量占全省60%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富硒产业带:经修复后的土壤硒含量达0.5mg/kg以上,培育出富硒小米、藜麦等功能农产品,品牌溢价超30%。这种“以水定产”模式使农业亩均效益提升至传统种植的4倍。
文旅融合激活滨水资源。沿桑干河开发的百公里生态廊道,串联起10个文旅景区:金沙滩生态旅游区将古战场遗址与湿地景观融合,年接待研学团体2000余批次;广武古城墙与明长城在滨水步道交相辉映;应县木塔周边形成“非遗”体验与有机农园结合的乡村度假区。2023年水生态旅游收入占全市旅游总收入38%,充分印证了“绿水青山”的经济价值。
人居再造:城乡融合的生态实践
“生态环境治理的终极目标应是提升人的福祉。”基于此理念,朔州将水环境改善延伸至城乡人居环境系统提升。
城市更新聚焦滨水空间再生。朔州老城改造中拆除河道违建12万平方米,新增滨水公园8个,形成30公里亲水慢行系统。七里河畔的煤运铁路旧址改造为工业遗址公园,保留龙门吊等设施讲述城市历史,成为市民休闲新地标。这种“留白增绿”让中心城区人均绿地面积增至15.6 平方米。
乡村振兴突出生态宜居导向。选择下马峪等30个村庄进行整村生态化改造:建设分布式污水处理站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,粪污经无害化处理转为有机肥;推广太阳能采暖、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,农村清洁取暖覆盖率达95%。最具特色的是雨水庭院系统:农户屋顶雨水经集流槽导入渗井补给地下水,形成微型水循环单元。这些举措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从15%跃升至80%。
文化重塑强化生态伦理培育。在右玉干部学院开设生态文明课程,将“右玉精神”融入治水实践;学校建立水土保持科普基地,开展“小河长”体验活动;传统节庆中融入生态主题,如清明放流鱼苗、冬至冰灯节展示水资源保护装置。这种文化浸润使生态理念深深植根于市民生活。
长效之道:绿色发展的持续动能
在新的发展阶段,朔州水生态治理仍在深化探索。
前沿技术应用突破治理瓶颈。投资1.2亿元建设的水生态环境感知系统,集成水质预警、污染溯源、生态评估等模块;在恢河流域试点数字孪生技术,模拟不同调度方案对水生态的影响;开展人工增雨技术应用,年增雨量达3000万立方米。科技创新正从“治标”迈向“治本”。
制度体系优化保障长效运行。出台《朔州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,确立生态保护刚性约束;建立GEP(生态系统生产总值)核算体系,将生态价值纳入政绩考核;探索水权交易制度,允许节水企业转让用水指标。这些制度创新为可持续发展构筑长效机制。
区域协作拓展放大治理效应。推动晋冀蒙交界区建立“永定河上游生态联盟”,联合申报国家山水工程;与北京密云水库建立跨境保护机制,实现生态补水与水质保障协同。生态共赢理念正突破地理界限,形成更广域的治理共同体。
在神头泉群的监测站,技术人员读取着水化学实时数据;桑干河畔的观光带里,骑行游客在杨树林荫道穿行;乡村污水处理站旁,农妇用处理后的中水浇灌菜园。这些日常场景共同勾勒出水生态治理的现实图景——当节水器具成为工厂标配,当有机农田取代撂荒坡地,当湿地公园承接市民休憩,朔州实践揭示着深刻的转型逻辑: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,在于将生态要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系统,使绿色不仅成为发展底色,更是生长于斯的生存方式。
朔州的故事仍在续写。随着“四水四定”原则的全面落实、生态产业化路径的深度探索,这座曾经“因煤而兴”的城市,正以治水为支点撬动全方位的绿色变革。
当9月的晨雾从桑干河面升腾,阳光穿透薄雾照亮蜿蜒的河道,那波光中跃动的不仅是水流的光影,更是一座城市在生态觉醒中破茧重生的信念与希望。